揭秘明末名將李成梁放虎歸山 最終引火自焚
明朝中后期的三大支柱:南有戚繼光,北有李成梁,中央坐鎮(zhèn)張居正,被稱作是明帝國(guó)的鐵三角。今天,我們來說說這位功過爭(zhēng)議最大的北角星李成梁。
李成梁,字汝契,號(hào)銀城,有考證說其祖籍本為隴西,祖上于唐末為避戰(zhàn)亂舉族遷入朝鮮。爺爺李英于嘉靖年間歸附明朝,任職鐵嶺衛(wèi)指揮僉事。明朝武官實(shí)行世襲制,李成梁少年便“英毅驍健,有大將才”(《明史·李成梁傳》),本應(yīng)繼承指揮僉事份的職位,可是到他這一代,家境貧寒,竟然籌集不到去北京承襲官職的路費(fèi),以至到了四十歲,還只是一個(gè)普通的“諸生”!
就在李成梁幾乎要對(duì)前途產(chǎn)生絕望的時(shí)候,他遇到了命中貴人。遼東巡撫御史很賞識(shí)他的才略,對(duì)他的處境非常同情,慷慨解囊,資助他進(jìn)京,這樣,他獲得了祖輩傳下來的職位。
這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(公元1566年),李成梁正式走上了歷史的大舞臺(tái)。
而在嘉靖中葉,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孫,達(dá)延汗(又稱大元可汗)巴圖蒙克“賢智卓越”(《李朝實(shí)錄》卷一七五),控弦達(dá)十萬(wàn)騎,建左右兩翼六個(gè)萬(wàn)戶,分別為:察哈爾萬(wàn)戶、兀良哈萬(wàn)戶、喀爾喀萬(wàn)戶、鄂爾多斯萬(wàn)戶、土默特萬(wàn)戶和永謝布(哈喇慎、阿蘇特)萬(wàn)戶。
不久,察哈爾舉部東遷,駐牧于薊、遼地域(大體相當(dāng)于現(xiàn)在的遼寧、內(nèi)蒙古東部和河北北部地區(qū)),“時(shí)窺塞下”,從此與明朝開展了曠日持久的激烈地廝殺。
可以說,變患頻起的北方給李成梁提供了展現(xiàn)戰(zhàn)略武功的機(jī)會(huì)。
李成梁以一名低級(jí)軍官的身份,經(jīng)常“親自搏戰(zhàn)”,沖鋒在前,在刀劍拼殺里,在鮮血迸濺中,在無數(shù)死人堆里殺出一條血路,冒死前進(jìn),贏得一場(chǎng)又一場(chǎng)戰(zhàn)功,換來了官職的不斷升遷,很快就升任為遼東險(xiǎn)山參將。
隆慶元年(1567年),又升為副總兵,協(xié)守遼陽(yáng)。
隆慶四年(1570年),遼東(指遼河以東地區(qū),今遼寧省的東部和南部)韃靼辛愛部入侵,遼東總兵王治道戰(zhàn)死,李成梁受任于危難之際,領(lǐng)總兵官,署理都督僉事。這個(gè)職位,自隆慶四年(1570年)至萬(wàn)歷十九年(1591年)一共做了二十二年,后因御史彈劾而解任。
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二十二年里,李成梁幾乎是無日不戰(zhàn),年年殺敵無數(shù)。在萬(wàn)歷十六年(1588年)之前,李成梁“師出必捷,威振絕域”(《明史·李成梁傳》),戰(zhàn)功層出不窮,令人眼花繚亂,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萬(wàn)歷44年進(jìn)士、天啟初年兵部職方員外郎,安徽桐城人方孔照所作的《全邊略記》。
正是這數(shù)不勝數(shù)的戰(zhàn)功使李成梁成了遼東的一根定海神針。
其面對(duì)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,無論是他們單獨(dú)挑釁還是聯(lián)合出兵,都一一將之挑落馬下,進(jìn)而拓疆七百里,建寬甸六堡,并在開原、清河、撫順等地開辦貿(mào)易市場(chǎng),與當(dāng)?shù)夭柯浣⒂押藐P(guān)系。
在明將吏貪懦,邊備廢馳的時(shí)代,李成梁縱橫北方邊塞,史稱“邊帥武功之盛,兩百年來所未有”。
遼陽(yáng)百姓稱李成梁的中左所之戰(zhàn)、盤山驛之戰(zhàn)、卓山之戰(zhàn)、平虜堡之戰(zhàn)、紅土城之戰(zhàn)、養(yǎng)善木之戰(zhàn)、鴨兒匱之戰(zhàn)、雕背山之戰(zhàn)、遼河之戰(zhàn)、阿州之戰(zhàn)、撫順之戰(zhàn)、沈陽(yáng)之戰(zhàn)、開原之戰(zhàn)、襖郎兔之戰(zhàn)、曹子谷之戰(zhàn)、古勒寨之戰(zhàn),射王杲,誅速把亥,擒逞、仰二奴,斬阿大、阿海,“皆萬(wàn)世之功”(《明史·李成梁傳》)。
憑借著這些赫赫戰(zhàn)功,李成梁官職不斷升遷。特別是萬(wàn)歷十年(1582年)斬殺泰寧部部長(zhǎng)速把亥之役,“速把亥為遼左患二十年”,是大明帝國(guó)北方的心腹大患,此人死,兀良哈部元?dú)獯髠硪粡?qiáng)勢(shì)部落海西葉赫部,經(jīng)分化瓦解,則在萬(wàn)歷十七年(1589年)被征服,首領(lǐng)那林孛羅請(qǐng)降。
可以說,斬殺泰寧部部長(zhǎng)速把亥之事是影響歷史進(jìn)程的大事,其影響之一是:明帝國(guó)、蒙古、女真三方的力量變化開始出現(xiàn)微妙的變化;影響之二是:帝國(guó)支柱張居正也因?yàn)樵诖似陂g對(duì)李成梁的鼎力支持而進(jìn)太師,從而成就了由張居正、李成梁和戚繼光三人組成鐵三角支撐帝國(guó)的繁盛局面。
然而好景不長(zhǎng),幾個(gè)月之后,萬(wàn)歷十年(1582年)6月20日,一直力挺李成梁的張居正溘然病逝,李成梁作為邊將,朝內(nèi)沒有保護(hù)傘,作戰(zhàn)趨于保守,以致于在萬(wàn)歷十七年、十八年、十九年連續(xù)損兵折將,戰(zhàn)略上一退再退。
萬(wàn)歷十九年(1591年)三月,李成梁發(fā)兵出鎮(zhèn)夷堡潛襲板升,初戰(zhàn)捷,回師途中遭伏擊,大敗,陣亡者達(dá)數(shù)千人。
此戰(zhàn)結(jié)束,李成梁不堪御史的彈劾,卸任遼東總兵,“以寧遠(yuǎn)伯回朝”。
從每戰(zhàn)必勝到連戰(zhàn)連敗,張居正的辭世只是一方面原因,另一方面,則完全是李成梁的自身原因。
《明史·李成梁傳》說其“始銳意封拜,師出必捷,威振絕域。已而位望益隆,子弟盡列崇階,仆隸無不榮顯。貴極而驕,奢侈無度。”想當(dāng)初,李成梁大才難展,白白憋了四十年,一登戰(zhàn)場(chǎng),自然“銳意封拜”,意氣風(fēng)發(fā),舍生忘死,而在“位望日隆”后,就耽于享受,“貴極而驕”了。當(dāng)然,誰(shuí)也不可能永遠(yuǎn)年輕,畢竟,到了萬(wàn)歷十九年(1591年),李成梁也已經(jīng)六七十歲的人了,你還指望他每天滿懷豪情地拎著刀子去砍砍殺殺也不現(xiàn)實(shí)。
另外,“軍貲、馬價(jià)、鹽課、市賞,歲干沒不貲,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。以是灌輸權(quán)門,結(jié)納朝士,中外要人,無不飽其重賕,為之左右”,如果以萬(wàn)歷十年(1582年)為分界的話,可以說,萬(wàn)歷十年(1582年)以后的李成梁已經(jīng)成為了一名活脫脫的地方軍閥了。
對(duì)于明末軍隊(duì)的作戰(zhàn)能力,呂思勉先生在《呂著中國(guó)通史》說:“軍事的敗壞,其機(jī)實(shí)隱伏于成梁之時(shí),這又是其一例。軍隊(duì)的腐敗,其表現(xiàn)于外的,在精神方面,為士氣的衰頹;在物質(zhì)方面,則為積弊的深痼;雖有良將,亦無從整頓,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。”
在呂老先生看來,對(duì)于明末遼東邊防的松弛,李成梁負(fù)有不可推卸的責(zé)任。
當(dāng)然,僅僅因?yàn)檫@個(gè)就認(rèn)定李成梁是“亡明”始作俑者,證據(jù)是不夠充分的。事實(shí)上,在李成梁的身上,還發(fā)生了許多不為人知、或者說是罕為大多數(shù)人所知的事。
其中之一,就是他和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間那些說不清、道不明,卻又千絲萬(wàn)縷的關(guān)系。
早在萬(wàn)歷二年(1574年),因?yàn)榻ㄖ菖嫣斍跬蹶秸T殺明朝裨將裴成祖,李成梁提兵問罪,直搗古勒寨,斬首千余級(jí),將罪魁禍?zhǔn)淄蹶健皺戃囍玛I下,磔于市”。
這也是一件歷史大事。
說實(shí)話,李成梁能順利活捉王杲,跟大明安置在女真里面的線人王臺(tái)、覺昌安、塔克世等人是有很大關(guān)系的。而覺昌安、塔克世就是努爾哈赤的祖父、父親。
剿滅了王杲,努爾哈赤和弟弟舒爾哈齊被擄到了李成梁軍中。李成梁不但不殺他們,還好生優(yōu)待了他們一番。這里所說的優(yōu)待,可不是一般的優(yōu)待,黃道周在《博物典匯·建夷考》中說:李成梁“撫努爾哈赤與速爾哈赤如子。奴酋稍長(zhǎng),讀書識(shí)字,好看三國(guó)、水滸二傳,自謂有謀略,十六歲始出之建地”。可以說,李成梁差不多是拿努爾哈赤哥倆他們當(dāng)干兒子看待了,老熟人的兒子嘛,畢竟。
差不多同一時(shí)代的明朝人王在晉也在《三朝遼事實(shí)錄》中說:努爾哈赤祖、父“因兵火死于阿臺(tái)城下,(其)方十五六歲,請(qǐng)死,成梁哀之,且虜各家救書無所屬,悉以屬奴”。
明末人茅瑞征所著《東夷考略》也記:“哈赤,伶姓,建州枝部也。祖叫場(chǎng),父塔失,并從李成梁征阿臺(tái),死于陣。成梁雛畜哈赤,哈赤事成梁甚恭”。
雖然黃道周、王在晉等人所記是從道聽途說中來,書中所記就存在有很多錯(cuò)誤和自相矛盾的地方,但李成梁和努爾哈赤的關(guān)系未必便是空穴來風(fēng)。
李成梁以后出征剿捕女真人,經(jīng)常帶著這哥倆。每當(dāng)這時(shí),努爾哈赤總是表現(xiàn)得很活躍,很勇敢,仿佛天生打仗的料,爭(zhēng)著打頭陣,屢建奇功,讓李成梁刮目相看。而在李成梁的指導(dǎo)下,努爾哈赤也學(xué)會(huì)了諸如布口袋、下套子、迂回包抄等等本事,仗打得有聲有色。而且,他和李成梁的幾個(gè)兒子也混得很熟,感情很好。
如果日子就這樣過下去,天下應(yīng)該不會(huì)這樣多事,可是李成梁并不想讓努爾哈赤一直在自己手下混。因?yàn)槔畛闪河X得努爾哈赤的各方面條件,都很符合自己在遼東推行自己戰(zhàn)略路線的需要。
李成梁的戰(zhàn)略路線歸納起來有八個(gè)字,也就是:以夷制夷,恩威并施。雖然有王臺(tái)和覺昌安、塔克世父子這類人在充當(dāng)線人角色,但遠(yuǎn)遠(yuǎn)達(dá)不到“以夷制夷”的目的。而在李成梁看來,努爾哈赤有勇有謀,打起仗來敢玩命,對(duì)自己又對(duì)明朝顯得忠心耿耿,是個(gè)值得培養(yǎng)的對(duì)象,于是,將他們哥倆放回了建州。
當(dāng)然,《清史稿》沒有這樣寫,而是說:“太祖及弟舒爾哈齊沒于兵間,成梁妻奇其貌,陰縱之歸。”顯然,這種說法并不靠譜。
李成梁放努爾哈赤回女真,相當(dāng)于是放虎歸山,“明亡清興”的肇端便發(fā)軌于此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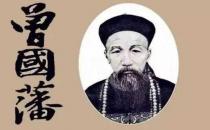



![歷史上的竇嬰是一個(gè)怎樣的人 漢武帝為什么要?dú)⒏]嬰](http://www.jewhye.com/uploadfile/2019/1124/thumb_210_130_20191124112618767.jpg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