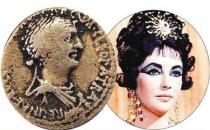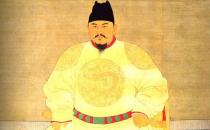解密:科舉制度在日本的發展為何會命運不濟 ?
“與其崇拜孔丘關羽,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”。
——魯迅的這句話,與其說是講給中國人聽的,不如說道出了近代日本人的心聲。
十九世紀,大清國與西方列強交手取得完敗。大清國的完敗,以軍事失敗為開端,但其實最深痛的慘敗在于政治及文化。這一切,日本看在眼里,記在心頭。
中國的科舉制,日本曾經頂禮膜拜,以為“最先進的選拔干部制度”。在黑暗的中世紀,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“三公”(公開公平公正)的“偉大創舉”。官是考出來的,人人皆有準考資格。中國的科舉制,那應該是封建官僚制度中最具“含金量”的部分。
效仿中國科舉制,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頒布《大寶律令》,搞了“貢舉”,所謂“貢舉”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。
然而,這項創舉自誕生以來,就沒有解決好兩個難題。或者說,根本解決不了兩個難題,這是科舉制的先天缺陷,也是導致其最后死亡的真正原因。
后人在總結科舉制死亡的原因時,多指這種考試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。誠然,這是科舉制死亡的一個原因,但只是表象原因。
科舉制死亡的致命原因,不在于后天,而在先天。考題的僵化是死亡的表象原因,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死亡深刻原因。
以“完善的文官制度”而言,中國雖然首創科舉制,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,“最大的官”和主考官問題并沒有解決。在“最大的官”——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,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,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。科舉制比起沒有“準考證”、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,是進步。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余年壽命,但在“強盜”(明唐甄《潛書》語:自秦以來,凡為帝王皆賊也)主考的情況下,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。
中國科舉制在沒有比較、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,但到了近代,來自西方的選舉制和堅船利炮一起敲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,“洋才”發明了“議會”,“首相”或“總統”是第一要“選”的官,主考官是百姓選民。憲政制度下官員們的執政水平和行政效率顯然要高出科舉許多,相形之下,科舉制的生命力,已到了垂暮之年,只能“自行了斷”。這是議會制對科舉制的優勢與勝利。延至后來,議會選舉制加公務員制,上下公平的選拔制度,已是大勢所趨。
早在中國進入文弱的兩宋時代,日本就放棄了“貢舉”,善于洞察學習的他們,也許意識到了這種制度必然走向僵化。中國科舉制在日本并沒有生根發芽。告別貢舉后,日本一沒有放棄尋找新的干部選拔制度樣板。十九世紀末葉,他們終于找到了。
近代日本從中國不敵英國、科舉制不敵選舉的事實發現,議會是個好東西,于是立刻模仿學習。明治天皇于1885年實行立憲,建立了內閣制度,并于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,設立帝國議會,議會由眾議院和貴族院構成。依據《大日本帝國憲法》,眾議院議員由國民選出,規定年滿25歲以上、交納直接稅15元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。
1890年,日本召開了首屆國會——“萬事決于公論”。那是亞洲有史以來的“第一次”。與其說明治維新造就了日本近代化,不如說亞洲第一個國會令日本崛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