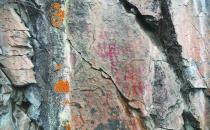西漢的馬政 漢武帝借以大規(guī)模反擊匈奴的基礎(chǔ)
漢朝同匈奴的百年大戰(zhàn),是人類古代史上規(guī)模最大的騎兵會戰(zhàn)之一。戰(zhàn)敗的北匈奴西遷歐洲,羅馬帝國還無力抵擋,這從另一個側(cè)面證明漢軍擁有當(dāng)時世界上最強的戰(zhàn)斗力。漢朝被稱為中國古代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,其興盛很大程度是由“馬政”為基礎(chǔ)的騎兵支撐,如李廣、衛(wèi)青、霍去病等名將都是騎兵指揮官。
騎兵橫空出世后,即成為古代歐亞大陸上決定勝負(fù)的關(guān)鍵兵種。步兵除憑借城郭、山險、水網(wǎng)和雨林等地勢之利,野戰(zhàn)絕難與之爭鋒。漢初天下甫定,江山殘破凋零,據(jù)載“將相或乘牛車”,馬匹奇缺可想而知。
劉邦以四十萬步卒抵御單于所率十萬勁騎,遭大敗后求和,此后漢室主要依托長城消極防御,并以假冒公主和財帛“和親”,以緩匈奴南下劫掠。經(jīng)文帝、景帝兩代六七十年休養(yǎng)生息,倉儲充實,牲畜大增。漢武帝登基時官馬即達(dá)四十萬匹,并出現(xiàn)“庶眾街巷有馬,阡陌之間成群”之繁榮景象,才有了建立騎兵集團與匈奴對等較量的基礎(chǔ)。
西漢初年,當(dāng)政者除大力養(yǎng)馬,又發(fā)展了馬甲、馬鞍、馬蹬,使騎手能騰出雙手交鋒,還能得到護(hù)甲保護(hù)。此時社會上層還有崇尚騎射之風(fēng),從皇家上林苑伴駕至民間聚會,豪門子弟都以驅(qū)駿馬競風(fēng)頭為榮。漢武帝依仗這一實力,于公元前133年對匈奴開戰(zhàn)。經(jīng)漢室?guī)状鲬?zhàn),至公元前36年漢軍攻陷郅支單于城,匈奴一部投降一部遠(yuǎn)遷,對長城以南農(nóng)耕文明的致命威脅至此消除。
漢匈戰(zhàn)爭期間,漢軍騎兵在速度、沖擊力、載動力和騎術(shù)方面都不遜于對手,數(shù)量還多于匈奴,從而改變了此前以步對騎、以慢應(yīng)快的被動局面。漢軍擁有龐大的騎兵集團,又能通過歷來步兵難以逾越的長城外數(shù)百公里缺水地帶,一再向漠北草原出擊,就此有了寓防于攻的主動地位。
公元前119年,漢武帝下令實施的最大一次出擊,動用騎兵14萬,步兵和運輸人員數(shù)十萬,還有運輸馬十萬匹。此役一度占領(lǐng)匈奴生息中心區(qū),迫其逃向“北海”(貝加爾湖)一帶,漢軍也因染疫和征戰(zhàn)死兵數(shù)萬、亡馬十萬匹。
武帝晚年派李陵北進(jìn)時,只能給五千步卒,結(jié)果遭匈奴騎兵追攻覆沒,證明馬匹經(jīng)久戰(zhàn)消耗巨大,漢軍不得不停頓攻勢以恢復(fù)經(jīng)濟并補充馬匹。為取得“汗血馬”改良馬種,武帝還不惜派兵千里遠(yuǎn)征大宛,“馬政”已成為當(dāng)時頭等戰(zhàn)略產(chǎn)業(yè)。漢朝經(jīng)百年持久消耗戰(zhàn)終于擊敗匈奴,也是優(yōu)勢經(jīng)濟實力支撐的馬業(yè)勝利。
漢武帝消除外部威脅主要依靠勁騎,對內(nèi)統(tǒng)治又首創(chuàng)“獨尊儒術(shù)”,重文輕武的迂腐之風(fēng)此后逐漸開始侵蝕上層。西漢末年和東漢中期的人口都發(fā)展到六千萬以上,古人又沒有科學(xué)的生態(tài)觀念,從《漢書食貨志》可看出中原的森林、草場多被耕田擠占,內(nèi)地養(yǎng)馬既缺草料又無馳騁馴養(yǎng)之場。東漢時馬匹數(shù)量已較西漢減少,戰(zhàn)馬則主要靠西涼(如今甘肅、寧夏一帶)供應(yīng)。此時劉氏朝廷對各地豪強的控制能力大為下降,已萎縮的養(yǎng)馬業(yè)和騎兵又被地方軍閥掌控。
公元189年,在黃巾造反促成地方割據(jù)形成的紛亂之中,野心勃勃的董卓率領(lǐng)擁有國內(nèi)最強騎兵的西涼軍進(jìn)入首都洛陽。后人傳說的赤兔寶馬,便在這支勁騎之中。袁紹等各派軍閥都以步兵為主,同西涼軍不敢交鋒,僅有曹操與之一戰(zhàn)也立遭大敗。董卓及其部將依仗這支國內(nèi)最強的騎兵集團,將漢朝皇帝作為傀儡并劫持西行,還毀滅了洛陽和關(guān)中地區(qū)。此后,中國陷入了長達(dá)四百年的割據(jù)混戰(zhàn)和社會經(jīng)濟大倒退的黑暗時期,直至隋唐時期才恢復(fù)到漢朝全盛時的人口、馬業(yè)水平,社會歷史的進(jìn)程為之付出慘重代價。
戰(zhàn)馬就是裝備。恢宏大漢,興也馬政,衰也馬政。建立龐大騎兵北擊匈奴獲勝,中國封建經(jīng)濟進(jìn)入第一個繁盛期方得到基本保障。漢末不重馬政,對這一古代具有頭等戰(zhàn)略意義的產(chǎn)業(yè)疏于經(jīng)營,不可避免地導(dǎo)致軍力大衰及天下大亂之悲慘結(jié)局。為禍之烈,莫此為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