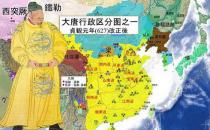外國軍官評辛亥革命時義軍 軍紀渙散的烏合之眾
1911年11月18日,北洋軍在馮國璋的指揮下猛攻漢陽,武漢的革命形勢開始變得異常的嚴峻。早在20天前,黃興、宋教仁、李書城等即抵達漢口,參與湖北軍政府的管理指揮。11月3日,黎元洪特意為黃興舉行了登壇拜將儀式,以此來鼓舞革命軍的士氣。但是,軍隊的養(yǎng)成非一二日之功,等到上了戰(zhàn)場,優(yōu)劣立現(xiàn)。所幸的是,海軍不愿為清廷作戰(zhàn)而陸續(xù)投效革命陣營,這解除了一個很大的隱患。
據(jù)租界內(nèi)觀戰(zhàn)的外國軍事專家觀察,北洋軍的士兵看上起結(jié)實、健康,有軍人榮譽感,軍中有良好的團結(jié)氣氛,指揮官能有效的控制各自的部屬;他們的機槍射擊術(shù)不錯,工程兵裝備良好,炮兵陣地的布置也恰到好處,但炮擊技術(shù)大有改進的余地。相比而言,革命軍的劣勢是顯而易見的,據(jù)外國目擊者的回憶,革命軍中因太多新招募而缺乏訓練的士兵,他們在進攻的時候雖然很勇敢,但那些受過訓練的老兵往往被安排在后面的新兵射殺。在北洋軍炮擊漢陽的時候,革命軍炮兵也積極還擊,毫不退縮,但炮彈從未落到鐵路上清軍的炮兵連隊里。
據(jù)民國將領(lǐng)陳銘樞的回憶,武昌起義爆發(fā)后,南京陸軍中學傾向革命的學生們在他的帶領(lǐng)下奔赴武昌參戰(zhàn),其中就有蔣光鼐、陳果夫等民國聞人,但真正上了戰(zhàn)場后,才知道戰(zhàn)爭的殘酷性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。特別是漢陽之戰(zhàn)中,在北洋軍的猛烈炮火下,革命軍瘋狂后退,潰不成軍,“河灘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,隊伍爭先恐后的搶渡,因為人多,浮橋被擠斷,許多士兵落水,被河水沖走,幸而此時據(jù)守鐵路線之敵,未繼續(xù)追擊,否則我們將全軍覆沒。”
澳大利亞第六輕騎兵隊的一位軍官對廣州、上海、蘇州、武昌和南京的革命軍進行考察后認為,除少數(shù)例外,革命軍大多是一群“軍紀渙散的烏合之眾”。這個評價雖說刻薄,但對于一群新招募而未經(jīng)訓練的軍隊來說,未嘗不是事實。據(jù)這位軍官的判斷,如果北洋軍全力支撐清皇朝,革命軍將不是它的對手。就軍事觀點而言,與其說革命軍戰(zhàn)勝了清廷,倒不如說北洋軍背棄了它。
雖然革命軍隊指揮無方,裝備拙劣,但他們勇敢而積極的戰(zhàn)斗精神贏得了普遍的贊揚,這也是外國專家們一致公認的。在漢陽之戰(zhàn)中,革命軍軍官傷亡兩百余人,士兵傷亡三千余,足見戰(zhàn)斗之激烈,軍心之可用,而這也是武昌起義后第一場真正的惡戰(zhàn)。據(jù)事后總結(jié),革命軍有湘軍前來助戰(zhàn),兵力本在北洋軍之上,而海軍亦在革命軍一邊,但黃興指揮行軍知進不知退,全軍盡布一線,后備無一兵一卒,全憑士氣向前攻擊,在左路湘軍進展順利時,臨時招募的右路鄂軍遇驚而亂,見危而潰,側(cè)翼動搖,以至于三軍盡潰,不可收拾。由此可見,軍事指揮是一門科學,非軍校、軍營出身的業(yè)余人士不能掌控,漢陽之敗,足見一斑。
“明月如霜照寶刀,壯士淹兇濤。男兒爭斬單于首,祖龍一炬咸陽燒。偌大商場地盡焦。革命事,又丟拋。都付與鄂江潮”。黃興初來武漢時意氣風發(fā),但在漢陽敗北后知勢不可為,他提議仿當年太平軍放棄武昌之例,湘鄂兩軍順江而下攻打南京。黃的提議遭到了湖北革命人士的強烈反對,指揮者之一張振武甚至拔槍怒喝:“頭可斷,武昌不可棄!敢言退者,莫怪我手下無情!”黃興見事已如此,只得于11月28日悄然離鄂往滬,他的那首《山虎令》,也就暫付“鄂江潮”了。
相關(guān)文章
推薦閱讀
- 1盤點日軍王牌師團的最終結(jié)局 哪個師團最幸運?
- 2揭秘中國遺憾結(jié)束朝鮮戰(zhàn)爭原因 斯大林突然逝世
- 3小記者改變大歷史 張作霖竟間接死于記者之手
- 4宋朝良將何其多 妙計建水上長城抵御北方騎兵
- 5唐宋時“踏白軍” 歷史上最早的職業(yè)偵察兵
- 6抗戰(zhàn)中的朝鮮獨立志士 奮斗在抗戰(zhàn)的第一線
- 7相差258萬多人解放戰(zhàn)爭到底殲滅多少國軍?
- 8國軍抗戰(zhàn)時期投敵人數(shù)竟然超過殲日人數(shù)
- 9國軍上校眼中的戰(zhàn)后日本是啥樣?經(jīng)常被美軍欺負
- 10國軍的奇恥大辱 抗戰(zhàn)勝利前一個月丟失18座縣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