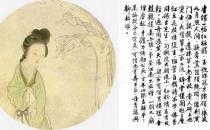元朝的“白宮” 馬可波羅記述元大都城墻為白色
在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中,記載了元代老北京城墻,令人驚訝的是,他明確地寫道,它被涂成白色。
元大都城墻東西7400米,南北長6650米,周長28.6公里,高約10至12米,完全由夯土制成,外面沒有包城磚,采用的是宋代筑城法,即在墻內先設永定木,然后再加橫向的纴木,然后加土夯筑。
由于北京夏季多雨,土城墻容易被雨水沖刷浸泡、導致倒塌,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議以磚石包覆,但因財力不足而作罷。后元廷專門抽調軍隊,負責收割蘆葦、編織葦席,每年入夏以葦席覆蓋城墻墻體,稱為“葦城”,民間俗稱“蓑衣披城”。后因懼怕起義百姓放火焚燒葦席,終止了“葦城”之舉,改為每有墻體松垮塌方時臨時征調民夫修補。
元城墻從建設到今,已有700余年,經長年雨水剝蝕,所剩無幾,目前只存西段、北段遺址,共計12公里,高僅剩2.7—7米,為植被所據。
可見,這種土墻就算涂成白色,遇雨也會被沖刷干凈,且中原歷來沒有給城墻涂白的習慣,因白有喪的意味,老北京唯一涂色的城墻是紫禁城,用的是紅色。
難道是馬可·波羅看錯了?
其實,在馬可·波羅那本大名鼎鼎的傳記中,類似錯誤層出不窮,比如他說“整個城市按四方形布置,如同一塊棋盤”,但事實上,元大都是長方形;他說“城墻底寬十步,愈向上則愈窄,到墻頂,寬不過三步”,顯然也不準確;他說皇宮中裝飾著戰士的圖形和戰爭的圖畫,亦難找到證據;他甚至說宮廷的窗戶中使用了玻璃,更是有些匪夷所思。
最奇怪的,是馬可·波羅對盧溝橋的描寫,說它有24個拱,可盧溝橋只有11個拱,還說它橋墩用石獅子裝飾,但只要去過盧溝橋的人就知道,它橋墩上沒有石獅子,只在橋柱上刻有石獅子,馬可·波羅還說橋面上鋪了雕刻了花紋的石頭,這亦不符合事實。這些離奇的細節,讓人懷疑馬可·波羅是否真的到過盧溝橋。
曾有人認為,馬可·波羅說的是另一座橋,并非今天的盧溝橋,可按他游記記載的方位尋找,卻沒有發現新的古橋遺跡。可見,他說北京元城墻涂成白色,恐怕也不靠譜。
馬可·波羅自稱在中國生活了17年,還“管理”了揚州3年,但在他的游記中,關于中國的地名多是突厥語音譯,比如稱北京為“汗八里”,如果他真的被忽必烈任為官員,為什么不用蒙古語或漢語稱呼呢?
到目前為止,中文史料中還找不到馬可·波羅的任何證據,很多人懷疑其作品中所寫的種種,并非親身經歷,而是道聽途說的集合。當然,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原本已佚,目前留下的抄本多達140多種,不同人在抄寫中可能添入了新內容,但這也說明,這本書記載的內容未必可靠,引用時應多加小心。